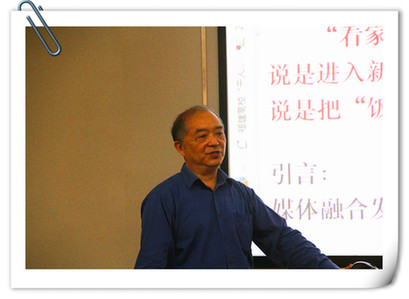顧勇華:和新聞打了大半輩子交道,還會一直繼續
視頻加載中... 從軍區報紙《人民前線》的編輯開始,走上新聞工作者的崗位,到新聞系的教師、副主任,再到歷任人民日報社華東分社總編輯室干部,專刊編輯部主任,人民日報社華東分社副總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顧勇華說自己學新聞、做新聞、教新聞、管新聞,大半輩子都在和新聞打交道。 如今已經年過六十的他,走進高校,和新聞系的學生談業務、論時事,帶來一場又一場多年經驗和潛心觀察提煉出的演講。 11月6日,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報告廳,“海西傳媒講壇進高校”第二場,主題《把“看家本領”用好用活——與新聞專業大學生談學理論、長本事》。這位資深“新聞人”的講桌上放著一個雙肩電腦包,一部新款的手機,還有一支大號放大鏡;臺下,是近百位教師和本科、研究生新聞學子。在思維縝密、互動頻繁的演講中,每一張演示都有錯綜復雜的鏈接,熟練操作著多媒體放映,顧勇華從新聞親歷者、管理者的角度為聽眾展示著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背后的故事,臺下不時爆發出笑聲和掌聲,互動環節氣氛熱烈。末了,對時間限制下來不及提問的同學,他說:“我把聯系方式給大家,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請多交流、多指教。” “部校共建:促進高校新聞學教育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路子” 聽說要接受一個訪問,盡管半小時后還另有安排,顧勇華還是答應了,他搬來一把椅子,讓兩位記者坐在他對面,“這樣比較方便,你們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問。” 自1999年開始,高等教育開始陸續擴大招生人數,其中以新聞專業招生人數最多。新世紀特別是近五年來,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求大大縮減,當被問及新聞專業學生人數那么多,但是從事新聞行業的人數卻可能一半都沒有的現狀問題時,顧勇華笑著說到:“一半?有三分之一來干新聞就不錯了!”,隨后,顧勇華嘆了口氣,說:“我們的新聞教育本身改革的步子并沒有那么快,”他認為,這一問題的出現不能僅僅歸咎于新聞教育改革本身,同時還因為新聞行業的需求改變了。顧勇華舉了人民日報的例子,人民日報每年招收新聞專業的人數并不算多,還有更多是法律、經濟或者外語等專業的畢業生,“為什么呢?因為媒體有自己新的需求,他們渴求新的專業人才。” 顧勇華認為,新聞本科畢業生數量龐大,然而卻面臨著知識受到肯定,但是能力不受肯定的現狀,其關鍵就在新聞教育和實踐是脫節的。“所謂的脫節不是說沒有實踐,而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實踐沒辦法和教育搭配起來。現在暑期學生們的實踐,記者直接帶學生做新聞,無法按照課程設計來安排實習。”在顧勇華的理想中,實踐應該是有實習計劃的,但他也承認這點在現行的實習安排中很少實現。對此,他認為的出路之一就是現在的 “部校共建”,這是條在黨委宣傳部的組織領導下,由新聞媒體發揮實戰優勢,促進教學與實踐相互融合的“新路子”。 “我們的新聞教育應該讓每個學生在本科畢業的時候都成為1.5個本科生!”顧勇華以福建省的優秀新聞作品為例,分析其競爭力來自于兩岸特色。他預測今后對于兩岸關系的報道需求會更大,廈大新聞學子應該牢牢抓住自己的這個優勢。“所謂1.5個本科生,這‘1’代表著一般大學生都有的素養和能力,而這‘0.5’是你的特色,是你尋找工作時重要的助力。”
“我也曾是記者,我知道記者們需要的是什么” 從最初的記者到如今記協書記處書記,身份的轉變對于顧勇華意味著工作重心的轉變。顧勇華說,他之前的工作就是集中精力辦報,而記協的工作是更好地為記者群體服務。 “做服務要有服務的意識,我以前做過記者,所以知道記者們需要的是什么。”顧勇華表示,在我國的體制下,很長一段時間里,無論是從職業地位還是收入來看,記者都是強勢方,但是后來記者轉為弱勢了,此時記協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幫助記者和記者行業。顧勇華在記協的這幾年以來,記協建立了記者的救助制度,即對因公殉職或者在采訪中受重傷的記者及其親屬進行救助。 在為慶祝人大新聞學院六十周年的一場學術論壇中,新浪網副總編沈亞川(筆名“石扉客”)在發言中表達了對新聞學界的不滿,他說,新聞學界沒有在媒體和記者們受到權力的壓力的關鍵時刻給予聲援,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對媒體報道操作層面的挑剔。對于這樣的看法,顧勇華認為這里所說的關鍵時刻的聲援其實是指當新聞業界面臨困境的時候,學界應該從理論上給出相應的應對方法。顧勇華想了一會兒,依然以新舊媒體融合盈利為例,說:“你看,這個題目現在業界炒得很熱,可是學界沒有給出相應的理論支持,如果走不出科學的道路,它就是不可持續的。” “講好中國故事” 講課過程中,顧勇華用了許多關于中國變化的報道案例,還不時以玩笑的方式指出報道中的紕漏之處,在每個版塊內容結束時都不忘問一句:“你們對于這個還有什么問題嗎?”在講座結束后的提問環節中,一位同學提問他關于“如何看待中國常常被指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問題。當被問及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時,顧勇華并未急于反駁,而是說了一段新聞發展的往事。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全世界媒體每天報道的中國負面新聞粗略計算約有一千多條。顧勇華問一位法新社的記者,“中國的發展你難道沒有看到嗎,為什么每天還是報道中國的負面新聞。”那位記者告訴他,“我們的記者只能遠遠看到停在天安門廣場的大巴,卻不知道開會的人在說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在北京城到處跑新聞,看到什么就報道什么。”十七大召開時,全國代表團大多都開放了,當時估算的每日負面新聞大約是六十多條。顧勇華說,還是那位記者告訴他,如今他想知道什么都能直接去采訪,沒有時間到處“亂晃”了。顧勇華認為,我國的開放效果是十分顯著的。在談到言論自由,顧勇華有點激動:“你們說,現在你們要說什么沒讓你們說,什么網上發不出去,但是我們國家對于有害言論的刪除和管理都太不及時!”他認為中國缺少的是對于新聞的依法且合理的有效管理。 中國是一座新聞的富礦,如何寫好屬于中國的故事,顧勇華認為,報道時,記者應該著眼于人民的長遠利益,這一點是報道時的根本關鍵。“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始終是個沖突,在很多普通民眾都為眼前利益奮斗時,我們要做的就是引導,去幫助開闊他們的眼界。” 文|吳玉琦 張肇祺 采訪|吳玉琦 張肇祺 攝影|劉曉宇 |